四川农村日报20260109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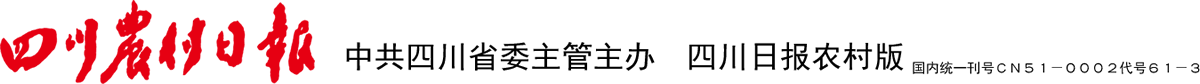


□许永强
当我走上都江堰玉垒山的青石板路时,天色正由灰转青。脚下石阶被千年雨水磨得温润,缝间生着茸茸的苔。耳畔是岷江不息的涛声。低沉的、持续的轰鸣,仿若大地深处的脉搏。
当地人上山不疾不徐,遇熟人便驻足闲话。我随其节奏,数至第一百零八级,抬头见玉垒阁飞檐自古柏枝桠间探出,翘角脊兽沐于晨光,似欲腾云。
此处望去,岷江划出果断弧线。江水切割山体形成的宝瓶口,宽仅二十丈,两千载光阴自此滔滔而过。当地人说玉垒阁是“万里长江第一楼”,其“第一”不在高矮,而在分量。站在这儿望出去,脚下流淌的是两千年岁月。
壹
石纹水痕的治水史诗
上古时,此山名“湔山”或“虎头山”,名中凝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大禹“岷山导江,东别为沱”,那开天辟地第一斧,相传便落于玉垒山岩脊。我用手触摸,石纹深陷如大地掌纹。当地学者说,此痕与岷江古河道变迁相关,传说与科学于此奇妙相遇。
真正的转折在公元前256年。秦蜀郡守李冰立于此山,所见当是江水肆虐、生民维艰。史书仅九字:“凿离堆,辟沫水之害。”立于宝瓶口旁,听雷鸣水声,方知这九字背后是数年艰苦卓绝的工程。自玉垒山体凿离的“离堆”,形成关键水道“宝瓶口”。此非普通开凿,而是人类智慧与自然规律的深刻对话:顺应水势,以柔克刚。自此,岷江一分为二,内江如血脉滋养成都平原,外江似臂膀宣泄洪流。玉垒山由此兼具双重身份:既是造化杰作,亦是人类工程的脊梁。
阁的雏形初现于唐代贞观年间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:“玉垒关在县西北三十里,贞观十四年置。”那时它该是座瞭望台,戍卒在此北望松州,南眺成都。晚唐宰相白敏中任西川节度使时,复修葺“玉垒关”,以守西陲。
我在山间寻找关隘遗迹。残存的石基隐在荒草间,石缝里开着淡紫的野菊。明代木刻图显示,玉垒阁原为三重檐歇山顶,与清代测绘图相合。数百年间,此阁于战火天灾中屡毁屡建。
2008年汶川地震后,清理瓦砾时发现三枚瓦当叠压:最下为汉代绳纹瓦,质朴粗犷,中为唐代莲花纹瓦,花瓣饱满,上为清代兽面瓦,怒目圆睁。它们来自不同朝代,却于最后一刻相拥呈现。
重建时,设计者决定保留一面“瓦当墙”。如今我站在墙前,看见那些裂纹如时光笔触,深浅不一的灰色是不同朝代的天空。新阁高46米,六层六角,形制仿唐。古建师傅说,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宋《营造法式》“材分八等”制度,柱网布局是典型的唐代殿堂式样。最妙的是,顶层观景台地面嵌一道玻璃。低头看去,下面正是原来的地基遗址。新旧之间,只隔一层透明。历史从未被覆盖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被看见。
贰
文学记忆中的时空叠影
761年秋,杜甫步履蹒跚登临玉垒山。个人流离之苦、家国破碎之痛,几将老人压垮。然极目远眺时,奇迹生发:“锦江春色来天地,玉垒浮云变古今。”十四字石破天惊。锦江春色自天地尽头奔涌,玉垒浮云于舒卷间改换古今。个人苦难遂获超越性升华。玉垒山自此不惟地理坐标,更成中国文学中一个永恒意象。
我特意选了秋日午后登阁。云时而聚山,时而散纱。忽一阵西风,云开处,成都平原如画卷铺展。陆游当年所见“烟树如荠”,原是真实。现代测绘载,自玉垒阁至平原视线高差518米,正合“下视如荠”之透视。
明代杨慎七过玉垒山,于《升庵文集》详记云象:“辰时见层云如楼,巳时化絮,午时散若罗纱。”对照当代气象记录:玉垒山清晨多辐射雾,上午蒸为絮状高积云,午后转透光层积云,完全吻合。此流放状元,于颠沛途中完成了一部诗意的气象观测。
山中现存十七株千年古柏,一一抚摸。年龄最老的那株,对应北宋熙宁七年(1074年)。那一年,苏轼兄弟沿岷江南下,开始了他们风风雨雨的仕宦人生。
清嘉庆《灌县志》录玉垒山诗词237首。“浮云”现189次,“江声”176次,“古柏”153次。数字背后,是无数如杜甫、陆游、杨慎之文人,于此寻得共同表达。他们观同一片云,听同一条江,抚同一棵柏。时光虽逝,情感共鸣穿越千年。
叁
古韵新声 立体叙事
登阁的过程,犹如翻阅一部立体的巴蜀文明史卷。
首层“千秋丰碑”,以沙盘模型演绎着都江堰从竹笼卵石到钢筋混凝土的演进。我蹲下身,看见微缩杩槎,中间填石,简单却巧妙。讲解员说,至今汛期仍会用到这种古老技术,“不是复古,是真的好用。”
二层“人文风流”,张大千的《长江万里图》气势磅礴,墨色山水间。我忽然看见一道熟悉的曲线,是岷江!转身看向窗外,真实的江水正闪着粼光。画中笔下与眼中景,在某个瞬间重合了。
三层“明月清风”,陈列民间传说的木雕栩栩如生:李冰化牛斗江神、二郎担山赶太阳……神话的想象力为严谨的水利工程披上了浪漫的外衣。
四层“唐风宋雨”最让我流连。这里复原了唐宋文人雅集:古琴名“松风”,棋枰上残局未解,茶盏里仿佛还有余温。
坐在蒲团上,闭眼倾听。风声、江声、檐角铃声。忽然明白:都江堰赐予蜀地的,不仅是“水旱从人”的丰饶,更是这份足以滋养诗心的安宁。没有这份安宁,何来“蜀戏冠天下”“蜀学比于齐鲁”的盛况?
及至登上顶层观景台,长风浩荡而来,衣衫猎猎作响。北望,龙门山脉层峦叠嶂,那是造山运动的力量见证;西瞰,鱼嘴将岷江一分为二,飞沙堰旋涡如花,宝瓶口束水如箭。整个都江堰工程如精密仪器,却又浑然天成;东眺,成都平原一马平川,城市天际线与田园阡陌交织;南观,岷江如碧玉丝带,在青城山影间蜿蜒南去。
此时回望,石砌的“玉垒关”就在不远处。一阁一关,并肩立于山巅:关是军事防御的产物,代表守护与坚韧;阁是文化观览的建构,象征开放与包容,既知“蜀道难”的险阻,更有“天府之国”的胸怀。
风从宝瓶口方向吹来,带着江水的湿润、平原的稻香,还有隐约的市声。玉垒阁檐角的铜铃响了,一声,又一声,清越悠长。
这铃声里,有杜甫的吟哦、李冰的斧音、历代重建的号子,有商旅马铃、诗人吟诵、游子叹息。它们碎成千万片,又合成同一支曲,一支唱了两千年的曲。
暮色渐合时,我缓步下阶。石阶在夕照里泛着暖光,像是被时光镀了金。走到山腰回望,玉垒阁的轮廓在渐暗的天色中愈发清晰,檐角剪影如雁阵,正要向夜空飞去。远处,都江堰的灯火次第亮起,沿着江岸蜿蜒成一条光的河流。而玉垒阁静静地立在山巅,如一盏不灭的灯,照亮来路,也照亮去路。